是否確如朱麗葉、福斯塔夫、愛德蒙、夏洛克以及許多其他莎劇中的人物聲稱的那樣,人在秩序井然的天下中所占有的位置不外是一件衣服或一個名號?就不能是腿腳、胳膊、皮膚、眼睛,或身體的任何一部門嗎?一個人若被剝光衣服,只剩下腿腳、胳膊、皮膚、眼睛或身體的其他部門,那他照樣原來的自己嗎?一個人若敢于舍棄一切排場,取消對天下、聲譽、頭銜、家庭的妄念,像他剛出生時那樣,赤條條地處于人世中,那他照樣他自己嗎?在本章一最先我就給出了自己的謎底。我以為莎士比亞并沒有一概而論。他將這一問題交給每一個悲劇人物來作答,性格各不相同的他們給出了迥然差別的謎底。
比如說,我們基本看不到“赤條條的”亨利五世,相反,他總是變換裝束,將哈利的衣裳換上君王的華袍。這身衣服他穿著是否合身另說,不外一旦披上,他就要擔負起這身華袍所代表的一切重任。他對福斯塔夫不光彩的背棄標志著換裝的終結。他在父親還在世時將王冠試戴在自己頭上則標志著他換裝的最先。那時他辯稱自己毫無惡意,只是想掂量一下王冠的份量。
簡直,他像在裁縫店試穿新衣的人一樣,只是試戴一下王冠。若把天下比作舞臺的話,他就是在帶妝彩排。哈利試戴王冠這一動作可以擴充為一個完整的故事:對哈利來說,他的王冠、華袍和權杖就像戲服,或像是笑劇中扮女裝的男孩子穿上的裙子。哈利正在帶妝彩排,他需要學習國王走路和語言的威儀——正式走上戲劇舞臺和歷史舞臺之前,他需要學習若何演好這一角色。上臺后,衣著得體的他就要投入演出,去飾演適合這身戲服的角色。
莎劇中絕大多數人選擇變換服裝,也有許多人選擇脫下衣服,另有少數人則在面臨殞命時赤裸一身。但赤身露體并不等同于面臨殞命時感應的 vanitatum vanitas[虛空的虛空],這既不是骷髏舞,也不是中世紀神秘劇。骷髏舞自己即是目的。面臨自己的虛無,他們并沒有找到自己的統一性,而是與之妥協,這是完全差別的生計性的體驗。赤身露體則是探尋統一性的最后一步。被剝得一絲不掛的人必須在赤裸中熟悉真實的自我,在知道自己赤身露體的情況下繼續生涯一段時間。
之以是云云,并不是由于他會一直衣不蔽體,莎劇中沒有哪個角色一直是赤裸的狀態,而是由于,被剝得一絲不掛,在赤裸中熟悉到自我,是人最基本的生計性的體驗。赤裸的人體驗到人類生計的本真,體驗到人生完滿中生計的偶然性,體驗到自己是天主隨便投擲的一枚骰子。李爾王的故事就是云云(霍姆[ Iran Holm]在英國皇家國家劇院出演李爾王時,就是赤裸著的)。
我無法在此對李爾多次蛻變的龐大性做出面面俱到的剖析,以是,我將集中討論從李爾讓權那場戲到厥后赤身站在暴風雨那場戲之間發生的事,聚焦他褪去衣服的歷程。讓權這場戲不僅意涵深刻龐大,而且有的解讀,至少從純粹生計性的角度,會推翻我之后對于李爾若何走向赤祼的所有敘述。若是從生計性的層面來解讀《李爾王》整部劇,可以把它讀成一則乞求被愛的故事。若是李爾為了乞求被愛而讓權,那他就更像愛德蒙而不像葛羅斯特。若作此解讀,則邪惡的愛德蒙和愚蠢的李爾都乞求被愛,二人也都在自己被人所愛的幸福感中死去。像在他其他劇中一樣,莎士比亞此時再次把情境推向極端。他讓惡毒的私生子和愚蠢的國王這兩個乞求被愛的人都死而無憾。
我頗認同這種解讀方式。只不外,李爾王和葛羅斯特以及和愛德蒙的相似點劃分出現在差別舞臺上。在政治和歷史舞臺上,他的遭遇和葛羅斯特類似;而在生計性的舞臺上,則和愛德蒙類似。當政治和歷史上運氣相似的兩個人(李爾和葛羅斯特)被拋入深淵時,他們同樣也登上了生計性的舞臺,這又是莎士比亞膽識過人之處。考特( Jan Kott)在《莎士比亞——我們的同代人》(Shakespeare,Our Contemporary)一書中將李爾與貝克特( Beckett)筆下的戈多( Godot)舉行對比,對那些只能想到生計性舞臺的人來說,這一對比頗有原理。貝克特筆下只有一個生計性的舞臺,但莎士比亞的《李爾王》中卻有兩個舞臺。
我現在只討論歷史舞臺上的李爾王是若何蛻變的,看看赤身露體的他若何從歷史舞臺走上生計性的舞臺。我也可以討論葛羅斯特的轉變,但他和李爾有偉大的差別。葛羅斯特是被人戳瞎,不是自己自動弄瞎的(像俄狄浦斯那樣)。打個比方說就是,葛羅斯特的衣服是被別人剝去的,不像李爾那樣是自己自動把衣服剝光。
布魯姆( Allan Bloom)在《莎士比亞的政治》(Shakespeare’ s Politics)中提到,李爾曾是個讓國家欣欣向榮的好國王,這一說法可能有些原理。他已往至少是個傳統的國王,不會自省,不會追問“我是誰 ”的問題,由于在他看來,他天經地義就是國王,基本無需質疑。第五幕中他甚至說自己“是個徹徹底底的國王”。他從沒想到,權力和威嚴竟有所差別。傳統上它們二者是統一的。他也從沒想到,他為了彰顯自己的特權放棄正當王位,效果卻是他也失去了使用暴力的權力,再也不能罔顧他人意愿而強迫他們做某些事。他放棄權力的同時,也不明就里地失掉了自己的威嚴。時代脫了節,發生了許多“違反自然”的事情,如后代們違抗父親。在李爾看來,考狄麗婭不屈從于父親的威嚴,這種做法也是違反自然的。
考狄麗婭簡直是個反叛者,她敢于冒著犯上作亂之名,在李爾王還大權在握時違抗父命。她對父親的愛不是儀式性的,而是一種不能用愛的宣言表達出來的情緒,是她珍藏在心里的感受,這對考狄麗婭來說是自然的,卻與李爾明白中的自然完全差別。李爾乞求從小女兒那里獲得愛,同時又堅決以為她深摯的情緒應讓位于自然權力。
李爾要求別人愛他,但在考狄麗婭的自然看法里,愛不能被下令,康德厥后也重復了這一看法。可見,在《李爾王》的第一場戲中,兩種自然觀就已經發生碰撞,但李爾還沒意識到這一點,他還沒有陷入兩難處境。即便他意識到了兩者的沖突(他對考狄麗婭的愛或許就已經是另一種自然的顯示),他也不愿認可,堅決抵制。或許正由于云云,他才想要聆聽愛的宣言,而不愿接納一種全新的、反傳統的、(對他來說)惹人惱火的愛,這種愛不聽從下令,不順從權威。即便李爾稱得上是個好國王,他也仍是個僭主,由于他容忍不了自由,容忍不了恣意的善( freedom of goodness)。他厥后被逼著直面恣意的惡即是為此支出的價值。
李爾這位從不自省的傳統國王,注重不到時代脫了節,不知道法定權力并不等同于事實權力。他意識不到,一旦他放棄了事實權力,就會同時失去他還不愿完全放棄的法定權力。由于失去了特權和軍權,他迫不得已違反心愿。只管他還擁有法定權力,但只能受制于事實權力。
時代脫了節。這個冥頑不化、自以為是、無邪輕信的老人本可以透過最愛的小女兒對他的反抗注重到時代的轉變,但他的無知讓他越發頑固。在這樣要害的時刻仍然不去思索,只能說真的是愚蠢。李爾是個傻瓜,但他的傻與波洛涅斯或馬伏里奧的傻差別。他的愚蠢中沒有笑劇身分。這種盲目無知的愚蠢異常危險。只有他身邊誰人并不愚蠢的弄人和忠心的隨從肯特( Kent)才會劈面告訴他這一事實。
當肯特前來侍奉已遭大女兒荼毒的國王時,李爾問他是誰。肯特答說:“一個人,先生。”(《李爾王》 1.4.9)肯特也對兩難處境毫無察覺,在他看來只有一種自然,那就是傳統。“一個人,先生”之以是主要,是由于它顛倒了這句話一樣平常的意思。對肯特來說,回覆“一個人,不外是一個人”實在正是偽裝的說法。他真正的身份是肯特伯爵,但現在卻偽裝成“一個人”。當李爾問他為什么要來侍奉自己時,他說李爾的神情之間有種氣力,讓他自愿稱其為主人。李爾問:“那是什么?”肯特只用了“威嚴”這個詞來回覆。對肯特來說,李爾雖失去事實權力,其威嚴卻沒有絲毫減損。他照樣原來的樣子,照樣國王。他也仍像國王那樣行事,例如唾罵毆打他女兒的仆役。他并不控制君王的怒氣。
直到面臨康納瑞爾時,他才最先意識到自己什么也明白不了了。
這時李爾才第一次詰責自己的統一性:“這兒有誰熟悉我嗎?這不是李爾。李爾是這樣走路,這樣語言的嗎?他的眼睛那里去了?……誰能夠告訴我我是什么人?”
弄人答說:“李爾的影子。”(《李爾王》 1.4.208 - 213∕四開本 220 - 226)弄人反映機敏,回覆準確。
李爾最初詰責自己的統一性,是由于他不能再維持原來的儀仗。從這一意義來說,他簡直是李爾的影子。從他對康納瑞爾說的最后一句話就可以知道,他簡直云云。
他說:“你以為我一輩子也不能恢復我的原來的威風了嗎?好,你瞧著吧。”(四開本 1.4.302 - 304)
他此時仍堅信自己能從國王的幽影變回真正的國王。
對李爾來說,釀成國王的影子首先意味著失去自我(即他是國王)。失去自我也就意味著失去整個天下。這樣會越過自我完全異化的界線,變得瘋癲。
他祈求:“啊,天呀,別讓我發狂!”(四開本 1.5.45)
厥后在里根家中,他又對康納瑞爾說:“女兒,請你不要使我發狂。”(四開本 2.2.376)
當里根把他趕出家門時,他罵道:“不,你們這一對傷天害理的妖婦!”(《李爾王》 2.4.437)
接著又對弄人說:“啊,傻瓜,我要發狂了!”(《李爾王》 2.4.445)
正是在這樣的情境下,他在暴風雨之夜離家而出。外面不僅是自然的暴風雨,它更有著象征意義(就像《暴風雨》中的一樣)。經由暴風雨洗禮的人已不再是剛剛奔入其中的誰人人。李爾已徹底蛻變了。他似乎有沐神恩,釀成了另外一個人。
前一場戲中( 2.3),為逃避追捕,愛德伽喬裝服裝成可憐的湯姆。他說:“可憐的湯姆!做他還不錯;我不再是愛德伽了。”(《李爾王》 3.3.186 - 187)
紋章經典版( Signet Classic edition)的編輯弗雷澤( Russel Frazer)在腳注中這樣注釋:“別人認不出我的話,我倒有幾分機遇活命。”它有兩層寄義:曾經的我現在什么也不是,因此別人將認不出我,我也認不出我自己。說著這句話,愛德伽便脫光了衣服。喬裝成這樣一個猥賤之人,愛德伽身上的一切已被剝光,誰都認不出他就是葛羅斯特正當的兒子。李爾也沒認出可憐的湯姆。但愛德伽說自己是“一個人”,并不像肯特那樣,是為掩飾真實身份,而是表明晰他的本質。
暴風雨這場戲在生計性的舞臺上上演。李爾的暴怒也如狂風暴雨般大作,詛咒著他那兩個忘恩負義的女兒。
但他也說:“我是受害大過于害人的人。”(《李爾王》 3.2.60)。
這是李爾第一次質疑自己。他雖以為女兒犯下的罪大過他自己的罪,卻也總算意識到自己有罪。
肯特接著說:“哎呀!光著頭呢!”(《李爾王》 3.3)
李爾最先光著頭,接下來,要連身上都精光了。
“我的頭腦最先昏亂了。”李爾說道。
,雙人雙吹風淋室技術參數
外行尺寸 1240×2000×2050 寬×深×高
凈化區尺寸 790×1890×1950 寬×深×高
過濾器凈化效率 ≥0.5um塵埃≥99.99% 鈉焰法
噴口風速 ≥27m/s以上方可達到除塵效果
風淋時間 0~99sec可調
循環風量 1600~2000M3/h
電 源 380V-50Hz或220V-50Hz
最大功率 1.5KW
重 量 460Kg
有隔板高效過濾器尺寸 610×610×120
初效過濾器尺寸 600×300×21名稱:人員進出無塵室所必需的通道,并同時起到氣閘室密閉無塵室的緩沖作用,是進行人員除塵和防止室外空氣污染無塵室的有效設備,也是目前凈化車間人員通的必需設備。
定義:為了減少由于人員進出所帶來的大量塵埃粒子,經高效過濾器過濾后的潔凈氣流由可旋轉噴嘴從各個方向噴射至人身上,有效而迅速清除塵埃粒子,清除后的塵埃粒子再由初、高效過濾器過濾后重新循環到風淋區域內,
他什么也明白不了了。[ 56]但實際上遠非云云。這時的李爾第一次生發出同情心:“可憐的傻小子,我心里還留著一塊地方為你悲痛哩。”( 3.5.73)
從下述這段臺詞中可以看出他的轉變。李爾發現赤身露體中蘊含著真理,他說:
衣不蔽體的不幸的人們 ……啊!我一直太沒有想到這種事情了。安享榮華的人們啊,吃點藥吧,到外面來體味一下窮人所忍受的苦,分一些你們享用不了的福澤給他們,示意上天是合理的。( 3.4.25 - 33)
此時我們感覺到,李爾脫掉了身上最后一件君王的華服。接著,扮成瘋子的愛德伽進場了。李爾說道:
唉,你這樣赤身裸體,受風雨的吹淋,照樣死了的好。難道人不外是這樣一個器械嗎?想一想他吧。你也不向蠶身上借一根絲,也不向野獸身上借一張皮,也不向羊身上借一片毛,也不向麝貓身上借一塊香料。嘿!我們這三個人倒是虛偽的了,只有你才是本來面目;赤條條的人不外是像你這樣的一個寒磣的赤裸的兩腳動物(著重部門由作者標明)。
李爾也扯掉了自己的衣服。接著,李爾四次稱愛德伽為“哲學家”,李爾需要他,需要與他為伴。有趣的是,現在他的朋友們反而明白不了他的做法。他們以為他已經失去了理智,未曾想他現在這般才是真正的蘇醒。李爾王詢問了有著“本來面目”的“哲學家”許多問題。
“讓我先跟這位哲學家談談。天上打雷是什么緣故?”( 3.4.141 - 142)
又問:“我還要跟這位最有學問的底比斯人說一句話。您研究的是哪一門學問?”( 3.4.144 - 145)
還說:“尊貴的哲學家,我們來作伴吧。”( 158)
“我要跟我這位哲學家在一起。”( 3.4.163)
“來,好雅典人。”( 3.4.166)
沒人能明白他,但我們可以。這兩個赤身露體的人看起來瘋瘋顛顛,是由于他們將自己剝得一絲不掛,但他們才是所有人當中最蘇醒的人,由于他們知道自己是什么。他們不外還原人的“本來面目”,是赤裸裸的人而已。
摘自《脫節的時代》
“我是誰?艷服服裝與衣不蔽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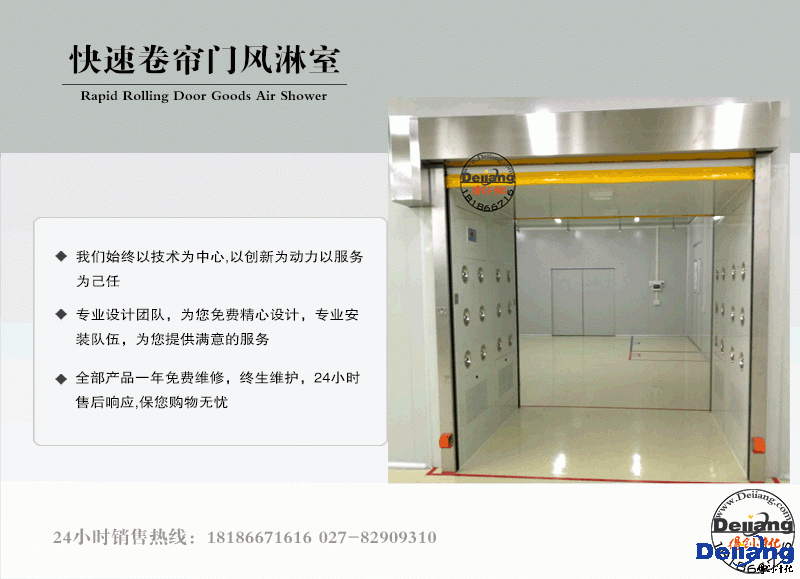


 服務熱線:1818-667-1616 027-82289886 彭經理
服務熱線:1818-667-1616 027-82289886 彭經理
 地址:銷售部地址:湖北省武漢市江岸區中一路華宇旭輝星空1棟1520室;工廠地址:湖北省東西湖區涇河三路
地址:銷售部地址:湖北省武漢市江岸區中一路華宇旭輝星空1棟1520室;工廠地址:湖北省東西湖區涇河三路





 客服
客服 